Seminar
在哲学系,讨论课一般是与基础必修课配套出现的,比如一门3学分的"中国哲学"课程,就会包含每周2学时的授课与平均每周1学时的讨论课。校方对这种安排引以为傲,每每要在公众号上介绍一下哲学系的课改成果时,总少不了夸赞一番讨论课,说什么“问题在一次次激烈论争中得到澄清,生活的边界在每一次思维突破中打开”,美其名曰授课与讨论、专业与通识教育相得益彰。
以我的经历来看,这种所谓的讨论课大多与浪费生命无异。讨论课上的同学们许多是几乎没怎么看阅读材料的。如何确定他们没有读?自己认真读了的人很容易能通过对方的发言来判断。如何确定他们几乎一点也没读?说来惭愧,当时的自己也往往瞎翻两页了事,然后惊讶地察觉到很多人还没自己翻得多,翻得认真。
不读文本,反而还不是最要命的地方,毕竟大学生都很忙,总有很多课是混过去更好的。只是,在这些讨论课上,我感受不到一丝对知识的热忱,甚至可以说他们对自己的发言,对所讨论的对象缺乏最基本的认真——用直觉与常识抒发一些似是而非的感想,亦或是发言就是为了炫耀那点可怜的学识,却从未想过“我想将这个地方弄明白”,更未想过要去自己学点什么。
我见识了很多开眼界的事情。他们可以确定“柏拉图的真实意图”亦或是笛卡尔没有犯下循环的错误——只因为老师与助教这样说过,可以对美国的政治与历史一无所知,没有一点民主生活的经验,却能恣肆纵意地比较德法美三国,大谈“真正的自由”与“人的解放”。我没有办法说服中哲助教,让他明白“现代物理学需不需要第一推动者”是个无意义的问题,或者是让他明白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开头究竟是“无极而太极”还是“无极生太极”是一个需要史料支撑的考据问题,而不是凭杨立华认为前者更符合朱熹的生生之理就能判断的。我也渐渐学聪明了,大三的西哲讨论班上,见到讨论休谟问题却连贝叶斯公式都写不对的助教,听到“在粒子物理学家看来,桌子这些物体都不是实体,微粒才是”1或者“这就像从苹果抽象到水果,又从水果复归到香蕉一样,学过马哲的人都知道”这种昏话的时候,也只是笑笑。
讨论课本不该是这样的。我见过很多科研出色的人认为大学课堂没有太大价值,也见到有些崇拜的朋友今天还发了朋友圈讨论技术课程该怎么学习的事情。其实除了自己啃书之外,讨论课是个很好的形式。选定一个大家感兴趣的主题,督促参与者每周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轮流由几位同学主讲这周的内容,遇到有不同意见的地方就随时停下来争论。在所有人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的情况下向真正有意义的问题纵深推进,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我认识到这点大约是在本科第三年的秋天,部分是因为我接触到了一些数院学长他们的讨论班,部分是我选修了一门叫“一阶逻辑”的课程,这是我在哲学系上过的最有意义的课程2。“一阶逻辑”与上文那些浪费人生的课程不同,名字里并不带“讨论课”,但它却是按照我说的方式组织的。学期初由邢滔滔老师开头之后,每周都由同学讲授当周内容。课程的要求是讲授中如果遇到自己没有理解,亦或是认为有错漏的地方,要当即打断并就这个问题展开,直到解决它为止。邢老师本人每周都会认真听完三个小时的报告,对每一个技术细节都不放过——有过一定数理学习经验的人一定都明白,即使是很熟悉、开了很多年课的内容,要做到这样也需要非常大的专注力与投入。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我误以为独立于符号集的推演概念是先于完全性定理的,以及混淆了N上的第一与第二数学归纳法,这两个细小到无足轻重的细节都被毫不留情地指出来了。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那个学期我的数理学习能力首次有了真正的进步。
而在一些同学的讨论中,尤其是一位数院学长身上,我看到了令我钦羡的东西。当遇到教材上并不存在,但联想到了的可能的结论时,他们会立刻开始讨论、思考,有什么想法就拿起粉笔在黑板上整版整版地写起来,其他人则会围在一旁梳理思路,仔细地核查有没有什么看起来是那么回事,实际上过不去的地方。在讨论范畴论中有关群的一章时,几位学长与钟老师就一个突然想到的问题争论了很久。这些人迅速地思考着问题,寻找一切可能的方法,挥动着手中的粉笔,生怕错过脑海中一闪而过的火花;不放过推理中的一丝漏洞,非要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不可。而当问题最终解决时,脸上则露出了纯粹的喜悦。我远远无法跟上,只能在一旁默默自闭,但那种对知识的热忱极大地震撼了我,这与我曾经在所谓的“讨论课”上见到的是多么的不同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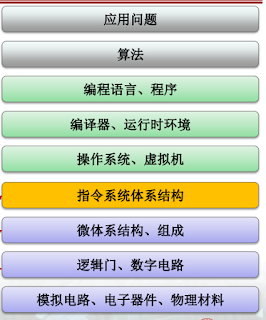
评论
发表评论